「第174记」
海沧地名考五:别被“表里不一”的地名欺骗了
随着分子人类学的快速发展,从基因的角度研究民族学、民系学已然成为文化研究的新方向。当直观、冰冷的血缘关系呈现于人前,以文化认同的传统认知开始遭遇巨大挑战,这点在南方诸汉族民系中表现尤为明显。
闽南人是南方各民系中汉族成分最高的之一,其从唐代以前保留至今的诸多风俗习惯,到底是古代中原主流传统的遗存,还是当地闽越人的影子,谁也说不清楚了。地理隔离让闽南与不断传承演变的中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差异,如方言发音和用字方面,近乎不同体系,以至于在地名方面,以闽南话和普通话对其解析,竟然会出现“表里不一”的结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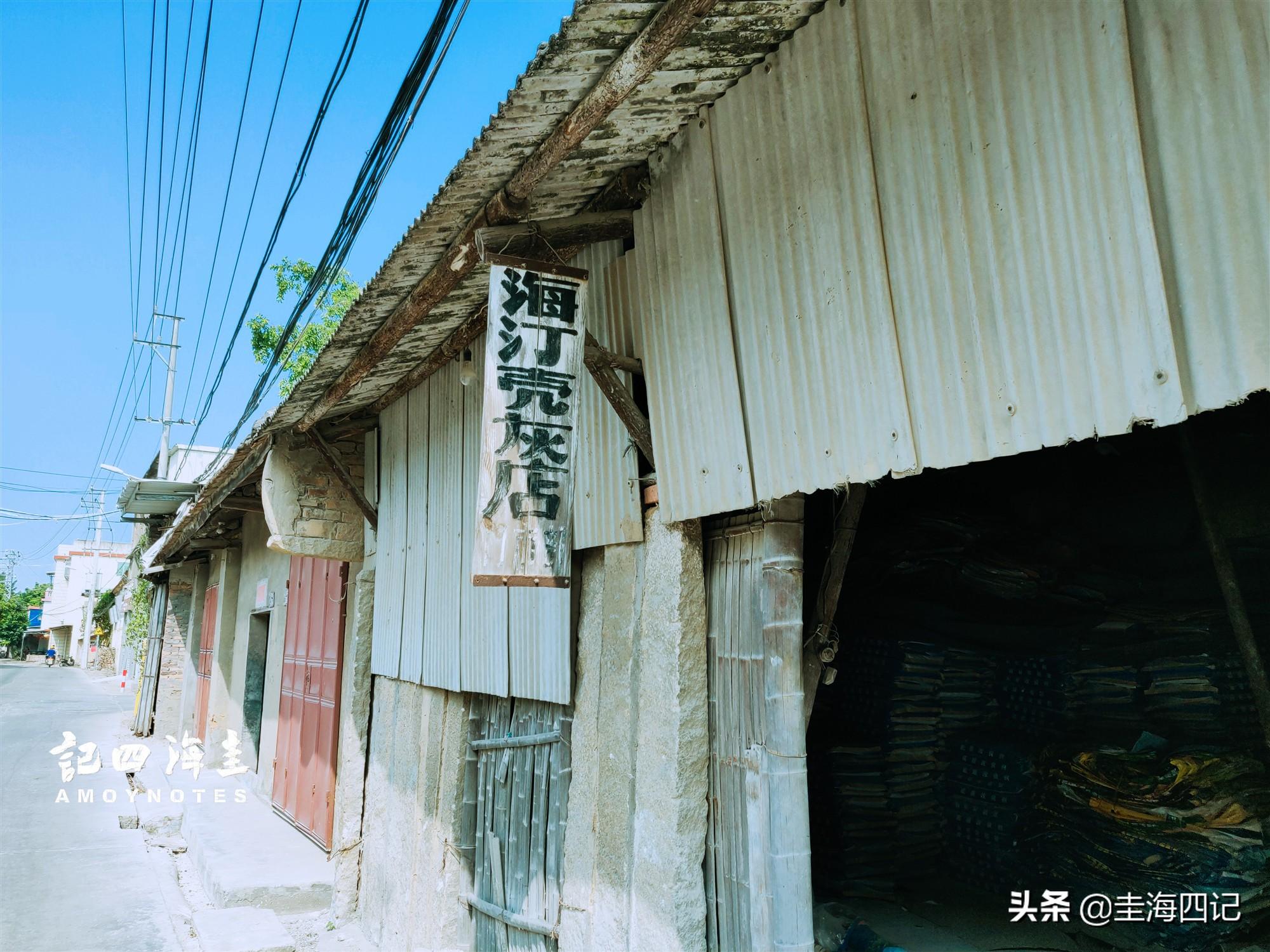
闽南语的文白混乱,海汀=海澄
起初,闽南各地方最早的定居者和经营者,往往以目不识丁或知识层次较低的百姓为主,他们战胜野兽和困难在某一地方开疆辟土后,首先会以简单易懂的名字为之命名,然后不断繁衍生息乃至壮大。故而这些地方的地名,往往具有鲜明的闽南特色。当新的移民或本土有文化的子孙达到一定规模时,为了乡族的发展,他们开始迎合朝代的主流,主动融入帝国的文化中,于是不同时期的地名开始有了各自朝代的痕迹,亦或者加入新移民的记忆。但这种变化,往往不是同时产生的,传统的叫法,和应世的写法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并存,因为在闽南基层社会中,文白读系统和口音、写法等本身就是并存的两套体系,闽南人对于这种兼而有之的做法相当有心得,以至于在地名上,很容易出现看到和听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,这便是“表里不一”的体现。
一、看不懂地名,先听听附近的叫法
钟宅姓“钟”,蔡厝姓“蔡”,这在闽南地区压根就不用解释,理所当然的事。但是,总也能遇到地名上的姓氏与实际居住的主姓不一的情况,如蔡塘不姓蔡,钟山不姓“钟”,对于这类案例,在理解上也不太困难,毕竟历史太长,战乱、瘟疫等,都可能促使某地方的人来来去去。然而,真正让人困扰的是,地名上一些用字,有时无法和传统叫法对的上号,这时我们可能要追问,是不是也是世事变迁的结果了?

钟山蔡氏家庙
闽南小刀会的发源地之一,曾属同安县的角美锦宅村,在当地也算是家喻户晓的名村。然而不太熟悉她的人,可能会把她联想为海沧锦里、杏林锦园一般的雅号,当你照着字面翻译成闽南话后,知道的人一定会帮你纠正的。原来,锦宅本是沈氏始居地,故名沈宅,之后黄氏入住并后来居上时,为了“去沈化”,将沈宅更名为“锦宅”,只是传统上的叫法被一直延续至今,这才产生了文不对音的乌龙。
与之相似的案例,如翔安区新圩镇的古宅,原名“辜宅”,黄氏聚居地;翔安区新圩镇的诗坂,原名“施坂”,陈氏聚居地;海沧区渐美村的芦坑,原名“卢坑”,谢氏聚居地。
二、找不到源头的地名,需结合姓氏匹配
乾隆《海澄县志》卷十九方外志载,“六社庵,在马垅,亭祀吴真人”,此六社庵匾额曰“慈济北宫”,民间俗称六社庵,乃马垅附近六社集资共建、重修的境主庵。据道光八年《重修北宫碑记》捐缘记录,以社为单位参与建设者计有六社,分别为龙塘、珠山、龙潜、化龙、凤山和南山,乍一看未知其所指,与周遭社村完全无匹配,然细细品味,这六社却都非本地俗称,而是广泛存在于墓碑中的雅号。因六社雅号在当地均有脉络可寻,要破解还算简单,如若出现地理或历史隔离,这找起来可就难了。

重修北宫碑记
依1929年《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》的分类,南洋华人一般被分成五大帮:潮帮、广州帮、福建帮、海南帮和客帮,除福建帮来自福建外,其他在当时均属广东。福建帮虽冠以福建之名,实则为操以闽南话的闽南人,他们多来自泉州和漳州两地,故而福建人在祖籍方面往往可具体到县,这也是人们用以区分城市别的依据。然而,在更早时的清代,在华人还未批量下南洋时,早先一步到达南洋的福建人,却仍保持福建原乡的乡镇、保甲籍贯,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渐渐成为土著华人,这些籍贯便逐渐被淡忘了。
如马来西亚清代墓葬中常见的东园,若追溯至闽南祖地,名为东园者不下十个,而论知名度当属龙海市东园镇,然结合墓葬中主人清一色的姓氏“林”,则并非此东园。后经郑来发先生考证,东园林氏乃今海沧新垵村林东社,林东社,因新垵区划变化,已与下叶、东张等社合并为东社,至今仍为林氏聚居地。据角美“教学儒”林氏记载,林氏开基祖由福州分居角美镇东美,至二世,大房居南园社,分衍墩上、桃洲、桥顶、南门等社;二房居东园社,即林东,与新垵邱氏一起,子孙遍布南洋;三房回迁福州。另依《槟城三都联络募捐善后序》记载,来自东园社的林氏计有两名,显然,东园林氏即来自林东社。
与之类似者,鹏程何氏即来自海沧坪埕,金沙周氏来自海沧后井(如为陈氏,则也可能来自角美沙坂,二者兼有),文山郑氏来自榜山文苑,峩山陈氏来自以东园过田俊美社为宗的俊美陈氏大支。
本文内容由作者:蔡少谦 提供




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