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粪尿是最好的肥料之一。旧时,把老市区的人粪尿拉到禾山做肥料,文人写成运粪,当地人叫着载肥。
东渡、湖里、殿前等处靠海,生产队用船只到市区载肥,他们要在码头边上修大粪池作为“中转”的地方。
大多数农民到城里载肥,用的是牛车、马车、板车或者自行车。牛马车板车装肥的肥桶是四方形的大木桶,木板的缝隙涂上桐油灰防漏。一个这样的肥桶能装10来担肥水,大约1000来斤重。那时候木材十分紧缺,要找到能做肥桶的木料还真不容易,坂美人甚至拆了清朝的牌匾做肥桶,令人痛惜不已!

运输肥料的牛车队(倪海 摄 《厦门日报》1955.2.19)
那时候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用牛车载肥,钟宅、刘厝、枋湖、洪水头也有用马车。赶牛车马车的人大多是半夜就出门,凌晨到市区收粪尿。人说“老马识途”,牛也一样,久了就会自己认路,赶车的人可以坐在肥桶上优哉游哉,甚至铺上稻草,美美地睡觉。赶牛车人睡觉也曾经碰到被人恶意捉弄,作恶者故意在半路上驱赶牛车调头,结果牛就把空车拉回原来的村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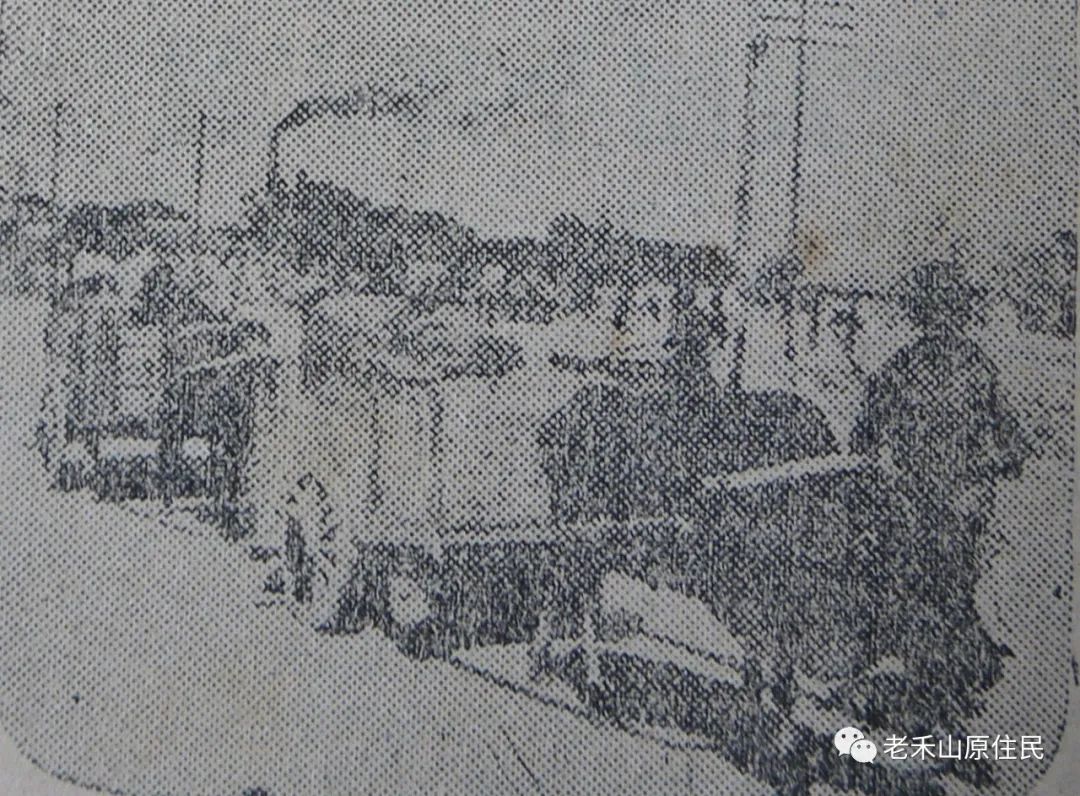
(枋湖)丰收合作社用牛车运送肥料(倪海 摄《厦门日报》1956.4.21)
人拉手推的板车,速度是快了一些,但是3个人一辆车,来回一趟市区,少说也有30多公里,连走带跑还要装肥,至少要四五个小时,空车还好,重车回来或者要经过莲坂、圆山,或者要经过祥店,或者要经过金鸡亭这几个长坡,弯腰蹬脚地使劲,夏天一步一滴汗水,冬天顶着东北风,雨天穿着蓑衣前行,艰苦程度可想而知。
那时候城区的柏油路只铺到双涵,其余是漫长的沙土石路。板车的车轮子小,轻便省力,但是轮胎在砂石路上容易破损,许多板车用上旧的汽车轮胎,耐磨耐损,不过无比笨重。碰上江头到五通的“银行坪”、到枋湖的“铁路坪”、到何厝的金鸡亭坪,3个人要使尽浑身力气才能把车子推上坡。

那时候时兴“支援农业”,市清洁管理处运肥到禾山的车队浩浩荡荡行进在厦禾路上(《厦门日报》1958.1.19)
自行车载肥用的是木桶,叫肥桶,车后座上驮着一桶,两侧各吊一桶共3桶,最难的是把上面那桶装上去,要有力还要有“势”。一车3桶装上粪水大概300斤重,又要骑车,既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。初学者往往把握不住车子,摔倒撞破肥桶,粪水撒了一地,臭气冲天,非常狼狈。有能耐的骑车人,甚至可以在后架上多装一只桶,多出的这一桶粪水是家里自留地上用的。那时,钟宅、县后、枋湖、五通、高林、后坑、后埔这几个大队都有自行车载肥的队伍,载着空桶下市区时,一路“叩叩哐哐”的声音,加上故意使劲按铃“叮铃铃”的响声,飞快急驰的车子也是那时的路上风景。乌石浦萧怣猛、浦口社王东规是用自行车载肥、运输的能人,力气大、技术过硬,用四只桶载肥,用自行车载四五百斤重的货,不在话下,赢得老禾山人有口皆碑。

难得有人保存下来的肥桶,那时也常用来装酒厂的酒糟、米粉厂的下脚料, 上面的二支横杆是为了能吊在自行车的后架上
解放后,粪尿由市清洁管理处、环卫公司经营,农民要先买“肥票”才行。文灶路口今加油站那个地方设了检查站,载肥的车子要在这里盖章销票。
旧时,市区人家几乎没有自用的厕所,提着便桶到公厕倒屎尿是每天早晚的必修课。公厕的水不让多用,所以屎尿掺水不多,“质量”上乘。但是,粪便的“质量”太好,容易发酵,会把肥桶的盖子撑开,也不是好玩的事。载肥的人往往在公厕争抢好的粪尿,就得比谁到得早,但是太早了还没到倒便桶的时候,也是白搭。用自行车载肥的人仗着自己行动方便,穿街走巷,国光府、麦仔埕、大王、局口街、山仔顶……一个个公厕探过,哪里有好粪水就往哪里冲。他们有时会辛苦一些,从第一码头装两桶海水到公厕使劲冲洗,冲下暗沟里的一坨坨粪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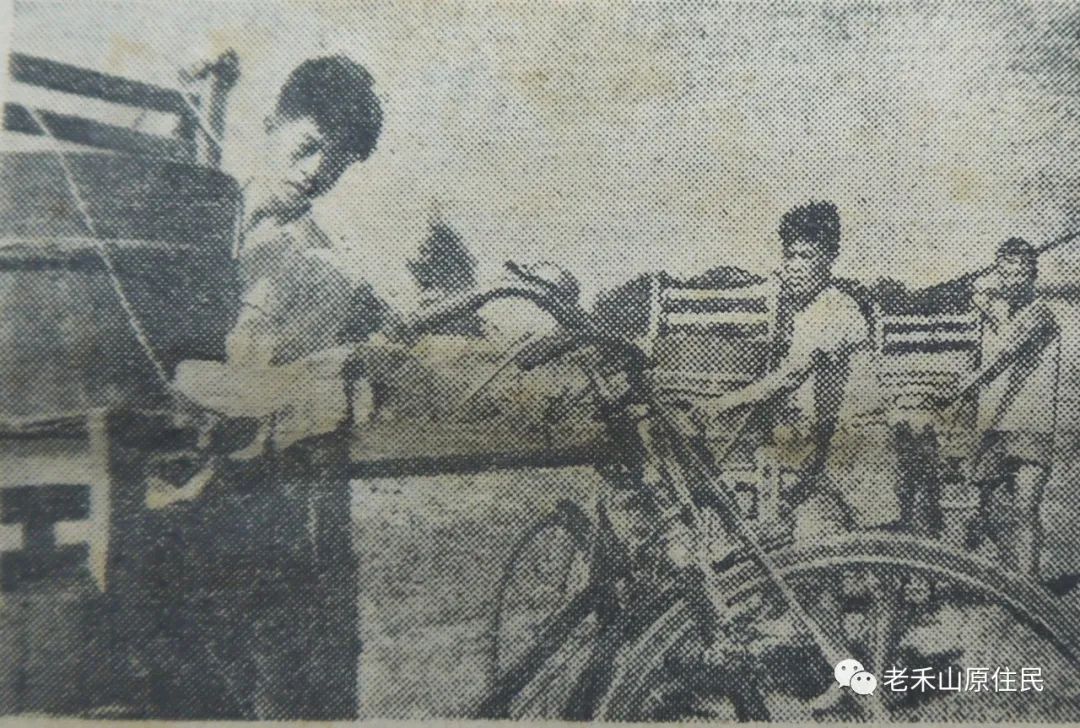
对敌斗争是英雄,农业劳动是模范。林边“23勇士”用自行车载肥归来(《厦门日报》1962.7.24)
如今,家家户户卫生间都有冲水马桶,屎尿进入楼盘小区的化粪池,变成污水送到污水厂处理,农民失去了最好的肥料,城里又增加了处理的成本。生活水平提高了,却失去了原本合理的循环利用,到市区载肥的景象已经是远去的记忆。起早贪黑、顶风冒雨,忍着恶臭,还要遭受市区人鄙视和另眼,禾山农民载肥曾经吃过的苦,没有多少人记得了。
经黄国富老师授权。
本图文内容转载于其关注号:老禾山原住民,版权归其所有。




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