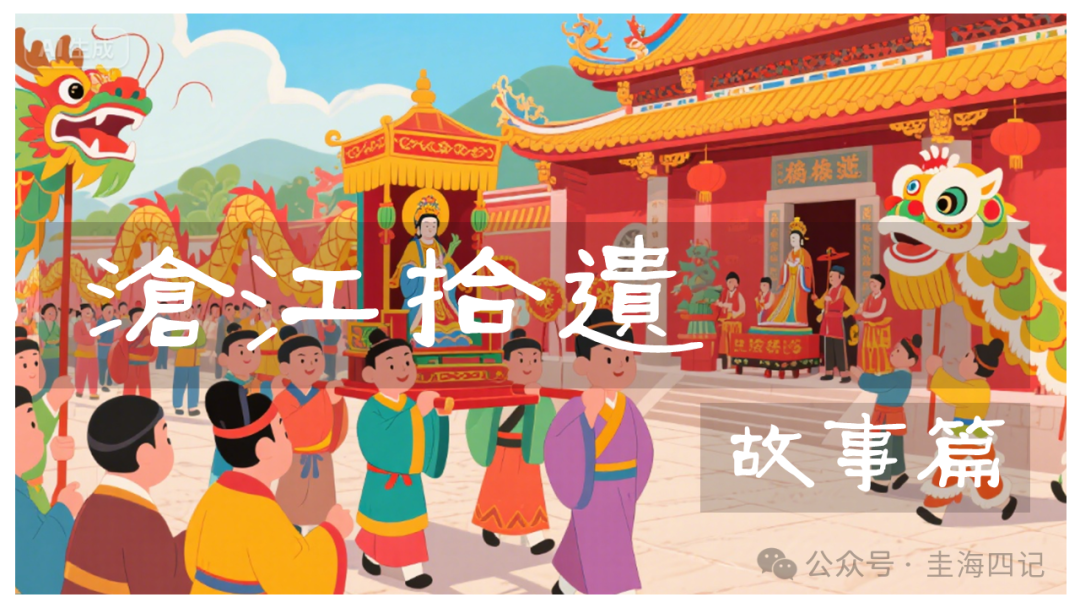
尽管柯挺生活的年代距今已经过去四百余年,但家乡的人们似乎未曾忘记这位大人物,每每谈到他,总有人能搬出各种版本的新奇故事。或许,除了他的成就外,还归功于他的“风水”传奇,为坊间的百姓增加了探秘的话题。
柯挺,自幼便刻苦专研风水学,年轻时便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,屡试不爽。万历三年,初取得功名的柯挺,被授以南乐知县。柯挺作为顺天府解元,其道学及文章造诣颇为当时文人所叹服,当他初到任南乐时,便想着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南乐县做点贡献,同时也积累点政绩。彼时,南乐县“科名久湮”,人心不向学,于是,柯挺便为学子们设计了诸多助学的方案,“一篑为山”便是其促学的成果之一。此外,柯挺认为,除了激发学子的内动力外,还需运用“风水学”为南乐县改命:

县城部分,一,将南北门由子午向改为西向;二,将东南隅的魁星楼重建为八卦楼;三,疏通城西街至关外道路,并于关头建叭蜡庙,于东关建迎春亭等。一番改建后,县城的物、气便通畅了。
儒学部分,在儒学前九曾河的南岸建云路坊,使人出入直上云路;前令曾将泮池移至儒学前,柯挺认为该举会导致“风气不宣”,故将之重移入儒学门内;又于明伦堂的土山上,筑造三台,其最高处再建聚魁楼,使明伦堂有所依靠,此外,为增加文风气质,又于楼边“栽三槐九棘,下立石刊一篑为山”,以为士子瞻仰。围绕着文庙周边,也做了改动,如将文庙后的敬一亭迁建于西侧;重修文庙东侧仓帝史皇庙的中殿,并于其厢房前置造书台,从而使文庙左右护卫双全。如此种种之后,南乐县竟一时人才济济,科甲频发,所拔士子皆取高第,柯挺的地师之名由此鹊起。
不久,柯挺便因南乐县政绩卓越而被擢升为陕西道监察御史。
万历十三年,朝臣针对万历寿宫选址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讨论,最终在以礼卿徐学谟为首的江南官员共同运作下,定址大峪山。起初,万历皇帝对此结果较为满意,但不久,即有大峪山风水不佳的谣言风起,他便开始动摇和犹豫了。为了坚定自己的选择,万历皇帝亲自率队往勘皇陵,此行也带上了擅长风水的柯挺。
初到大峪山,太仆寺少卿李植、光禄寺少卿江东之、尚宝司少卿羊可立等圣眷正浓的官员即上疏云大峪山下有顽石,不宜定为寿宫。大学士申时行即对曰:“李植等说,青白顽石大不是。大凡石色麻顽,或带黄黑者,方谓之顽,若其色青白,滋润,便有生气,不得谓之顽石矣。”此时,柯挺站了出来,自言习葬法,颇识风水,力争道:“若大峪穴下有石,臣敢以身当之。”吏科齐世臣也极力抗疏保大峪山之吉。其实,早在之前,嘉靖皇帝便曾想过把显陵由湖北迁往大峪山,后因群臣反对而搁置,显然大峪山的风水是有保证的,故而万历皇帝对大峪山已有偏好,只是碍于众说,不好表露而已。这次视察大峪山,有柯挺、齐世臣据理力争,万历皇帝便顺势传谕内阁道:“大峪佳美毓秀,出朕亲定,又奉两宫圣母阅视,原无与卿事。李植等亦在扈行,初无一言,今吉典方兴,辄敢狂肆诬搆,朕志已定,不必另择,卿其安心辅理。”后来,朝臣以柯挺、齐世臣有谄媚之疑,而戏称两位为“石敢当御史”、“保山给事”。
之后,柯挺在巡视完湖北后,即被提拔为南直隶提学御史,在此期间,他又一次展现了伯乐的天赋,所拔之士后来都成了晚明的肱股之臣,甚至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及第者代不乏人。人们在不清楚柯挺所采取的促学和选拔人才措施的情况下,只以“风水学”臆断这位神奇的御史,故而又称柯挺为“风水御史”。而就当柯挺志得意满时,一件诡异的经历,竟让他中道辞官隐居。

万历十六年,柯挺按例出巡。其母亲和一众子弟居住在提学府衙内堂,每到夜晚,总能听到惊悚的异响,家人们心惊胆颤、夜不能寐。在柯母的安排下,男女老少分作几个小群体,各集中于房间内,有力者或执明灯,或持杖棍,作防御状,待异响临近时,立即奔出,边敲打铜器边追着异响,其他人则循着铜声尾随而至。一行人,跟着追到了一堵墙下,异响便消失不见了。尾随者便照着墙根掘地,竟挖得一根相当长的异骨,旁边夹着不少鸡鸭的毛和血,此外竟无所获,众人惊叹之余又多生了几分恐惧。不久,柯母便生了一场大病,随后去世。柯挺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后,便一蹶不振,官运就此按了暂停键。于是,柯挺在为母守孝期满后,便辞官隐居于建安的紫霞洲。而柯挺的继任者,受灵异事件影响,不敢再继续住在提学府衙,便另立新署,以免遭灾。如此诡异,想是柯挺自断预知太多,有所惩报,遂不敢再逾越天机,遂就此隐遁,悲喜之间因果相报罢了。
END
本文内容由:蔡少谦 提供




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